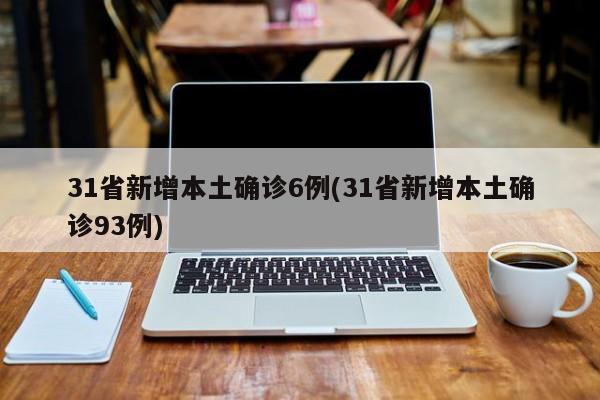人类交流或社会行为中,时常会出现一种新现象——人人都能识别,却无人能命名,因为尚无对应术语。人们总觉得需要创造一个新词。2015年詹姆斯·巴塞洛缪在《旁观者》杂志提出的"美德信号"(Virtue signalling)便是此类案例,而2019年罗布·亨德森在《纽约邮报》创造的"奢侈信仰"(Luxury beliefs)是另一例。
近日我看到议员彼得·凯尔接受天空新闻威尔弗雷德·弗罗斯特采访时谈及《网络安全法》,奈杰尔·法拉奇的名字被反复提及——因其宣称将废除该法案以保护言论自由。凯尔声称,此举让法拉奇彻底与吉米·萨维尔"站在同一阵营",成为儿童性虐待的支持者、协助者,与娈童癖为伍。弗罗斯特给予他重新措辞的机会,但凯尔坚持己见。对话就此终结。
我记得在脱欧公投后另一个场景:戴维·拉米接受安德鲁·马尔采访时,将保守党欧洲研究小组(ERG)成员称为"纳粹"。马尔略显错愕地给他收回辱骂言论的机会,但拉米反而强化指控,宣称ERG中的保守党成员"更恶劣"。
两例中,采访者都对这种诽谤性夸张修辞感到无措(即便未至哑然)。这些言论制造了恐慌时刻:"该进入下一话题了"——这正是人身攻击式转移话题的目的。将对象比作吉米·萨维尔虽不等同于新版"希特勒类比",但效果同样旨在贬损目标、引发恶感、进行排斥。
此类现象也体现于其他表述:若指出强奸团伙中巴基斯坦裔穆斯林男性比例过高(立即被斥"伊斯兰恐惧症!");捍卫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("恐同!");坚持跨性别女性不应关押于女子监狱("恐跨!TERF!")。
我们都识破这种策略,但其术语为何?我咨询了X平台的智慧。
"德语里可能有专有词",有人戏言。
Verleumdungszuschweigen(诽谤性沉默)。
这显然难以流行。
这属于人身攻击论证(argumentum ad hominem),但不止于此。这是人格羞辱,但未必虚假到构成诽谤:这种憎恶可能确实源于偏见或非理性恐惧,也可能归因于真诚的宗教、政治或哲学信念。"煤气灯效应"?不,这比之更精准。"归谬希特勒化"?不,那特指(字面意义上的)纳粹类比。C.S.路易斯创造的"布尔弗主义"亦不完全契合,因该策略并非针对心理状态,而是针对整体人格,乃至整个道德世界观。
这是一种动机谬误,但攻击者的意图是用极端恶劣的标签玷污发言者,迫使其禁声。通过断言道德缺陷、触发羞耻感,旨在引发听众或读者的愤慨与敌意。这种羞耻感理应诱发焦虑,让人为维护社会接纳性而立即急于否认威胁。
我认为这可称为"审查式污名化"(censory smearing)。
"Censory"并非审查(censor)或苛评(censoriousness),而是指被审查的感知。故"审查式污名化"是以"封杀此事"为目标的诋毁,即具有审查效果的夸张人格抹黑。
有些人深信自身信念优越或事业正义,必须压制所有持相反观点者。最有效的方式是指控对方偏执或"仇恨"。过去"偏执"标签颇有效,直到人们发现斥他人"偏执"者往往自身偏执。但新一代污名化策略不同:高喊"伊斯兰恐惧症""恐跨症""种族主义"等标签者,通常能凭借其受保护特征传递道德完美感或自义感。同性恋者或可被称"恐同",穆斯林或可被称"恐伊斯兰"(若多米尼克·格里夫的定义工作组按预期推进,确有人会被如此标签),但这般指控的效果,约等同于指责黑人是种族主义者。
无人愿被控为"某某恐惧症",或被"某某主义者"的污名诋毁,或被玷污为"仇恨者""否认者"(参见对纳粹大屠杀的否认指控)——即便其立场在概念上具批判性、科学上持怀疑态度、或完全无法信服。人人都希望显得道德,或以道德著称。当道德受质疑,会产生羞耻感、挫败感乃至公开屈辱。该策略如此奏效,以致有人失去生计与声誉,整个机构被攻陷羞辱至陷入根本性自我审查,甚至导致长期不公与重大伤害。
故下次当安德鲁·马尔和威尔弗雷德·弗罗斯特面对政客以傲慢姿态斥政治对手为"纳粹"或"娈童癖"(并宣称"此事毋庸再议"时),我希望能听到立即反驳:"这不过是审查式污名化。我们谈谈实质问题如何?"
下次若有人称你"种族主义""极右翼"或"法西斯",你可回应:"啊,这真是'审查式污名化'的绝佳案例——带C字母的censory;道德羞耻谬误。请允许我解释……"
为您推荐:
- 韩国最佳15种休息站美食:从地方经典到新晋人气之选 2025-08-27
- 居民自豪地在全镇悬挂圣乔治旗:这是爱国主义的体现! 2025-08-27
- 北京新增1例确诊病例 系此前确诊患者妻子 活动轨迹公布 2025-08-27
- 乔治王子面临重大转变,坦言"感到紧张" 2025-08-27
- 全国新增46例境外输入病例 疫情防线持续承压 2025-08-27
- “审查污名化”的兴起 2025-08-27